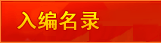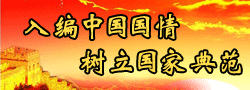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网是忠实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唯一综合性国家年鉴网,是为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做好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的有关精神,打造网上国史馆,推进国家史志信息化的建设的具体举措。中国年鉴网通过推出“阅后即定”等新技术,让历史能定时凝固下来,致力为每个行业、地区、单位、个人提供网上与移动历史空间,让每个行业、地区、单位以及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史记,都能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热点内容
推荐内容
网站首页 > 历史人物 >
杨月楼:一代“猴王” 的婚恋悲剧--中国年鉴网(2)
然而19世纪末的上海,已不同于中世纪的旧式城镇,租界的设立,移民的涌入,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社会[SheHui]原有的等级关系发生[FaSheng]潜移默化的变动。人们的身份[ShenFen]地位受到金钱利益的驱动,也在发生[FaSheng]改变。所谓“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官绅寒士贫儒蓝缕而自惭形秽”。这一[ZheYi]被时人感叹为世风不古的现象,恰恰反映人们的尊卑荣辱观念已经突破身份[ShenFen]的限制,发生[FaSheng]了深刻的变化。即以杨月楼来说,他的年收入比一般塾师高出十倍之多,他所以敢于接受韦女的婚约,也是因为经济地位的提高促使他渴望享有与良人平等的社会[SheHui]地位,争得与良人自由恋爱的权利。正是这种人权意识在婚恋观念上的觉醒,触犯了卫道士。因此,韦家的乡党族亲,对杨、韦的婚恋深恶痛绝,要求严加惩治,在社会[SheHui]上得到呼应。附和者并不仅仅是为了韦家的荣辱,更多地是为了使“优伶党毋以效由猖獗,所谓以一儆百”,“庶几其余优人,稍知畏惧”。所以,鄙薄艺人的,厌恶自主择偶的,反对良贱通婚的,维护既定等级不能[BuNen]逾越的,在杨韦婚恋的风波中纷纷登场。从中可见,这是中国[ZhongGuo]传统封建社会[SheHui]向近代化过渡中,尊卑贵贱等级序列失控后,在保守势力中激起的回应。
毫无疑问,在身份[ShenFen]地位已经淡化的市民中,对韦杨的婚事,持以同情的也大有人在。议论者认为:“孟子有言:食、色,性也。一优人耳,忽有配以美色之妇而不愿者,夫岂人情?一弱女耳,忽许配以合意之婿而不从者,妇岂人情?”“月楼身属微贱,有人肯嫁以女,岂有二、三其德?试思贫士当困顿之时,忽有配以美色之女,断无不愿娶之理,况月楼乎?闺秀当怀春之候,忽令嫁得合意之婿,岂有不愿从之理,况阿宝[ABao]乎?”因此主张“设身处地”观之,这是合情合理的事。韦女勇敢地在堂上抗辩,“不顾寒苦微贱,愿同生死”的爱情,更是博得人们的赞许。有的愤而指出:“窃玉偷香,士大夫、名闺秀,向有犯之者,而欲以发乎情、止于礼之道,望之于优人弱女,能乎不能[BuNen]?”然而韦姓家族与广东[GuangDong]籍的商人是一官商纠集的势力集团,杨韦的婚事在他们看来,是辱没乡亲的丑闻,坚持要求“正风化,攘奸凶”,指控韦女的母亲无权为女儿论婚嫁。由此可见,这一[ZheYi]案件从一开始就在身份[ShenFen]地位与人性观念上发生[FaSheng]交锋。
这一[ZheYi]案件还引发了中国[ZhongGuo]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上海知识分子与广东[GuangDong]籍商人乡党相互对峙的局面,这就是以《申报》为首的同情派与广东[GuangDong]籍商人乡党的重惩派之间的一场争论。
1873年在此案发生[FaSheng]后,《申报》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杨、韦的婚恋与公众的反映,起初多是附和传闻,虚虚实实,对杨韦也不乏有贬责之词。随着案件的审理,严刑逼供被曝光,引起舆论大哗。按照清律规定,以良贱通婚罪论处,只该杖打一百板子释放,实际审讯的情况是:“杨月楼于问供之先,已将拇指吊悬几乎一夜,甚至膀肩两骨已为扭坏,后皆不能[BuNen]使动……又用架以困之,架口最狭,将胫骨紧压,几至不能[BuNen]呼息。”这样残酷地行刑逼供,是依法断案?还是泄乡党的私愤?主张重惩的认为:“以乡谊同愤,况有亲叔主张”,杨月楼“污我粤人”,不严惩,不能[BuNen]泄愤。对这样徇情枉法之论,《申报》主笔拍案而起,顺应民情,转变立场,以“持平子”、”不平父”的笔名发表一系列的评论,抨击说:“在粤人以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为大惨人目。”责问县令以何根据施以这样的重刑?“上县既极刑以索供,至郡内又加刑以逼迫犯人不使翻其前供也。审人莫有不公于此,残忍之事从未闻有如此之甚也。”“中国[ZhongGuo]县官其肆私以残民,私刑以随私意而索供,其可忍乎!”批评广东[GuangDong]籍的乡党“代人为父”,公讼于官,是仗势欺凌弱小,“以合省正人而公讼一优伶、一奔女,何异以泰山之尊重而压一卵,以狮象之全力而搏一兔。”
这一[ZheYi]案件的审理在国内外都有影响,议论最多的是在华的外国人,他们认为中国[ZhongGuo]官吏“每于犯法之民,不论罪之轻重,动用非刑,毫无哀矜勿喜之心。”“(嘲)笑华人喜为非分之事,华官好用非法之刑。”《申报》鉴于官府的枉法行为有辱国家的尊严,特地发表《本馆复广东[GuangDong]同人书》,严正地指出:“杨月楼不过一优人已矣,而所出案情实为当今之大事也。固不以杨月楼一人所干而论也,以兆民之得失、国家之尊严两者所关系而论之耳。此案也非上海一隅之人所共为称论者耳,实在中国[ZhongGuo]十八省传扬已遍矣。非为中华一国内之人所谈论,经英京大新报名代默士(今译泰晤士)亦为传论,几天下士人无一人不知悉也。”
这样一件在国内和国际深有影响的冤案,发生[FaSheng]在一个颇有名气的艺人身上,又得到权威报纸《申报》和社会[SheHui]舆论的指责,只要官方还有一点理性和良知,也不能[BuNen]无视民情疾苦,草菅人命。然而,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发展到清朝末年,极度昏聩腐朽,官吏的贪赃枉法,乡党的结私舞弊,已经成为解不开的死结。这一[ZheYi]案件终于以官府的权力压倒社会[SheHui]舆论而结束,其结果是:杨月楼按诱拐条律判处充军,韦阿宝[ABao]被送到善堂(收容孤残、盲流,处理善后的社会[SheHui]组织)强制择配重新嫁人,《申报》也被迫停止了这项报道。
在中世纪的欧洲,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因家族阻扰,双双殉情,生不能[BuNen]婚配,死却遂了心愿;在19世纪末的中国[ZhongGuo],一对苦苦相恋的纯情男女,熬过了多少社会[SheHui]偏见和严刑拷打,却挣脱不了封建家族的魔掌,至死也不得两情相守,从此天各一方。
轰动一时的“杨月楼案”就此旗息鼓了,但却没有烟消云散。从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这一[ZheYi]月的《申报》所见,在主惩派和同情派论战的硝烟中,公众舆论终于在传媒中得到传播,市民中终于有了人权意识的萌芽,这是中国[ZhongGuo]前所未有的新事态;虽然这一[ZheYi]变化以力量对比的悬殊,没有得到胜利,但却捅开了封建体制腐烂的疮疤,埋下了渴望民主、公正的种子。
至于这一[ZheYi]事件的主人公后事如何,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追踪报道,所能知道的是,一代名优只活到41岁。